订阅
|
tvb云播在线看最热影视 https://www.yunmov.net 爆炸头、厚刘海、哈伦裤、紧身衣、渔网袜、超短裙...... 如果你是90后或者85后,你一定记得他们。 他们曾在虚拟世界建立起庞大的“网络帝国”,以独特造型穿梭于沿海城市的各个角落。 溜冰场、公园是他们的线下聚集地,流水线工厂是他们进城的唯一出路。 他们,曾因另类装扮遭遇全网“反杀”。 他们,是“被迫消失”的杀马特少年。 1. 2006年,一个11岁的男孩坐在只有十余台电脑的小网吧里,看着荧幕上色彩斑斓的世界满是好奇。 他的手指在键盘上肆意敲打,眼睛却停在那些个性张扬、略显颓靡的造型上久久不能移开。 后来,他了解到,那些吸引住自己目光的造型,被称为视觉系。 一天,趁着无聊,男孩拿着从网上下载的视觉系图片,来到村里一家美发店,要求造型师按图给他做发型。 一开始,造型师的表情明显有些懵,但还是试着给他做了一个红色的爆炸头。 做完发型,男孩又跑到两元店,买了一堆不知名的小饰品、染发水和化妆品,回到家开始鼓捣。 一系列操作完成后,他带着这身造型大大方方上了街。 男孩新奇的装扮,很快引来路人注目。 那是长这么大以来,他第一次感受到被关注的美好。 从那一刻起,他的生活从了无生趣中迅速剥离出来,进入到另一个炫酷世界。 他将自己鼓捣的造型上传到QQ空间,越来越多的人对他的造型进行夸奖和评价,甚至,他还有了崇拜者。 大伙儿都觉得他“酷比时尚”,于是他开始搜索“时尚”这个词。 发现“smart”之后,他决意将自创的造型命名为“smart”的谐音“斯马特”。 可“斯马特”听起来总归不够霸气,于是便有了“杀马特”。 名字取好了,男孩的第一个杀马特家族QQ群也建好了。 他把喜欢杀马特的人通通拉到群里,开始宣传自己的造型,并鼓励成员模仿他。 很快,只有小学文凭的他,拥有了几十个QQ群和至少20万人的杀马特追随者。 这个有着“杀马特教父”之称的男孩,就是罗福兴。 2. 罗福兴这个名字,在大众眼里是陌生的。 但在曾经热爱过杀马特的人心中,却有着特殊含义。 比起某种文化产物的创建者,他更像是某个弱势群体的连接者。 他和他身后的杀马特少年们,有着很多共同点。 他们大都来自偏远小镇,大都是留守农二代,他们没资源、没背景、没文化,却比任何人都想逃离那片寂静得让人发慌的土壤。 遗憾的是,杀马特兴起之时,没人愿意真正走近他们。 奇怪的发型、夸张的着装、廉价的饰品、浓浓的妆容...... 他们身上的一切,跟眼前这个世界相比,都是那么的格格不入。 即便拥有百分百的回头率,他们在大众眼里,依然是脑残、低俗、浅薄、没文化的代表。 仿佛所有贬义词,都能随意按插在他们头上。 但事实,真就如此吗? 2019年,导演李一凡耗时两年,采访78个杀马特人群,收集915段工厂流水线工人的生活录像,用纪录片的形式带我们还原杀马特群体的真实世界。 其中,杀马特文化的发起人罗福兴,是他的第一个受访者。 罗福兴,来自广东梅州五华县的农村,典型的90后。 两岁时跟着父母来到深圳,在他幼时的记忆里,深圳没有都市化的高楼大厦,只有积满灰尘的建筑地和拉着横幅讨工钱的民工。 五岁多的时候,原本父母想让他在深圳念小学,但因户籍和年龄等因素,未能入学的他被送回梅州。 刚开始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后来又跟了外公外婆的他,大概从那时起,就已经觉察到自己的存在很多余吧! 3. 罗福兴的外公住在山里,离他们最近的一户人家,也隔了很长一段路。 父亲把他寄样在外公外婆家后,没再回来看过他,也从未往家里寄过钱。 母亲隔两个月会寄一千块给他,但回来的次数也不多。 外婆常跟他说父亲不要他了,父亲没用之类的话。 但在他心里,始终有一个位置是留给父亲的。 尽管他知道,父亲不止母亲一个女人,也不止他一个孩子。 他还是会想他,会记得他对他的好,记得他唯一一次陪他过生日的点滴。 那是母亲提醒后,父亲才应允的一次生日之约。 他放下所有工作,给他买可乐和蛋糕,带他放风筝。 风筝的线总能牵引着风筝往前走,可父亲手里却没有那根牵引他往前走的线。 他常常盼着父亲来电,但父亲每次都没空。慢慢地,积攒的希望变成失落,就只能用无所谓来掩饰内心的渴望。 村里的年轻人都进城打工了,留下的只有孱弱的老人和不谙世事的孩童。 罗福兴记得,每当夏夜,寂静的村庄只能听到虫叫声。到了冬天,连虫叫声也没了。 无尽的孤独感油然而生,他唯一的念想就是赶快逃离这死一般的寂静。 大约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母亲将他接到奶奶身边,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老师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惹事。 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没人教他们如何去爱,没人教他们如何保护自己,更没人去倾听他们的心声。 记得有一次,罗福兴被村里的小孩骂,他没有回嘴,只是狠狠地瞪了回去,结果换来一顿打。 后来他把这事儿告诉母亲,母亲也只用“别惹他们”回应他。 4. 缺少爱的滋养和陪伴,亲情只剩敷衍和冷漠,罗福兴在试着习惯和渴望被关注中左右徘徊。 那之后,他挨了打,便用摔伤回应大人。 网络的兴起,为他空洞的世界打开一扇窗。 不管兜里是否有钱,他总能在网吧待上一整天。 上机时长用完他也不走,站在别人身后,看着他们上网也很快乐。 14岁那年,他辍学来到深圳,那是父母为生活奔命的地方,也是他为生活寻求希望的开始。 但很快,他就明白了这座城市对像他这样的人群,有多么的不友好。 文化低,年龄小,他能做的工作实在太少。 他在工地搬过砖,在工厂流水线做过工,也在理发店当过学徒。 他终于用微薄的收入撑起自己的生活,但他依然是那个被忽视的人。 只有玩杀马特的时候,他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在他的杀马特王国里,他是一声号令便能搅动风云的领头人。 他号召杀马特QQ群成员入侵其他群,占领百度贴吧、攻占开放性论坛、贴上杀马特图片、附上简介和QQ群账号。 他还发起线下活动,约上同城杀马特一起做造型、拍照、打游戏、溜冰...... 走红之后,有不少护肤品广告商邀他在QQ空间和微博上发广告。 那段时间,靠着杀马特小伙伴刷出来的点赞和转发,罗福兴挣了几万块。 拿着这笔钱,他找媒体写宣传杀马特的软文,剩下的基本花掉了。 没多久,罗福兴的微博账号因刷点击作弊被封。之后,再也没人找他做广告了。 事实上,从大肆兴起到被迫消失,关于杀马特的争议从未断过。 5. 即便在杀马特流行的那几年,罗福兴也经常遇到加他QQ只为辱骂他的陌生人。 因为杀马特,他收获了从未有过的人气,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谩骂和诋毁。 2009年到2012年期间,杀马特不断遭遇“反杀”,罗福兴掌管的几十个QQ群,也面临着被瓦解的局面。 不仅在网上,现实世界同样容不下他和他的杀马特群体。 去工厂工作,杀马特发型是老板将他拒之门外的理由。 去美发店学美发,杀马特发型是顾客拒绝让他服务的理由。 对于寻常人来说,理想不过是现实的垫脚石。 对罗福兴来说,他连现实都够不着,又拿什么去谈理想? 他只知道,首先得活着。 为了活着,他的头发总在红与黑、长与短之间不断转变。 彻底告别杀马特,是在2016年。 那一年,他又爱又憎的父亲患了肝癌。 他一直以为,对自己不闻不问的父亲就算死了,他也不会难过。 当这一天即将来临时,他还是放不下。 他打电话告诉母亲,母亲坚决不回去,他只能独自去看望父亲。 父亲临死前,给了他1000块钱,那是他身上所有的家当。 那一刻,他对他生起了怜悯之心,他乞求老天让他撑到中秋,他想陪他吃一顿团圆饭。 但他还是走了,走在那个下着雨的夜里,走在那座漏水的瓦房里...... 他没有为父亲的离去流一滴泪,他也没再恨过父亲,他记着的都是他的好。 他说:“只要把我生出来就行了,我能看到这个世界,已经很幸运了。” 他是善良的,他比大多数诋毁他的人都要善良。 父亲的离去,让他明白他该扛事儿了,父亲的路不能在母亲身上重走。 6. 他需要给这个支离破碎的家一份安稳,于是他开了一家美发店。 但仅仅三个月,店铺就倒闭了。 再后来,导演李一凡找到他,邀他共同完成《杀马特,我爱你》的拍摄。 于是,他开始搜集杀马特图片、视频、联络杀马特旧友、凑齐采访...... 两年时间,一部为杀马特正名的纪录片问世。 片中受访的杀马特群体,有着和罗福兴相似的经历。 他们都是来自偏远地带的留守农二代,物资的匮乏、教育的落后、家庭的缺失,让他们小小年纪便没了生气。 他们中的大多数,没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便匆匆进了城。 他们进城务工的年龄,大都在11岁到16岁之间。 他们没钱、没学历、没背景,年龄也达不到用工要求。 除了办假身份证获取一份小型工厂的流水线工作,他们没有别的出路。 因为未成年,他们每天都要工作10小时以上,有时甚至加班到天亮,但得到的报酬却极少。 他们终于迈开走出大山的步伐,但城市的霓虹灯却从未对他们开放过。 他们生存的空间,永远是高楼背面的某个角落。 在家乡,他们是留守儿童;在城里,他们是不停运转的机器。 没人真的关心他们,老板眼里,他们是廉价的劳动力;路人眼里,他们是可有可无的透明人。 他们想为自己的世界添加一点甜,他们想证明自己是有血有肉的生命。 房子和车子对他们来说都太遥远,他们不敢想,所以他们打起自己头发的主意。 他们用奇特造型吸引路人的目光,只为有人多看自己一眼,多了解自己一点。 7. 哪怕引来的是谩骂、羞辱,甚至掐架,他们也愿意。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感受到自己还活着。 他们和罗福兴是一样的人,所以在杀马特的推动下,他们相遇了。 他们孤单的生命,终于有了同伴。这一刻,他们凹造型的目的不再是吸引路人,而是寻找同类。 有了同类,他们不再孤单,不再落寞,他们的青春从此有了色彩。 一起凹造型、拍照、炸街、聊天、溜冰、玩游戏......这样的日子,欢乐又自在。 但没过多久,属于他们的快乐便褪了色。 2013年,一首名为《杀马特遇见洗剪吹》的歌曲迅速走红,这首极具讽刺意味的歌让本就非议不断的杀马特遭到全网“反杀”。 那段时间,一些假杀马特也出来兴风作浪,他们戴着同样夸张的假发,无下限地搞怪和自黑,这些迷惑行为很快成为瓦解杀马特群体的利刃。 罗福兴用心经营的杀马特家族QQ群迅速解体,线上骂声一片,而线下的杀马特们也不好过。 他们不仅工作受阻,还会遭遇无缘无故的殴打,生活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杀马特,这个从未被正视过的群体,只能剪掉长发,换上“正常人”的装扮,回归到原来的位置。 他们有的还在工厂徘徊,有的已经回到老家,有的靠养斗鸡过活,有的靠养鱼维生,有的在城里做美发...... 如今,城市的街上,几乎看不到杀马特的身影,那些曾经为杀马特疯狂的少年,大多也都到了而立之年。 再看那时的自己,他们中也有人觉得傻,但唯一不变的是,他们从未后悔有过那样一段看似荒诞的青春。 8. 作为杀马特的发起者,罗福兴是少数还在都市停留的人,完成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后,他的收入来源是做头发、接外活,和偶尔的艺术展邀约。 杀马特的“反杀”风潮已过,人们对异于常人的审美也多了一份包容之心。 受“杀马特教父”的影响,还是有不少人愿意找罗福兴做杀马特造型。 但他们不再带着这样的装扮去炸街,大多数人完成造型出去走一圈,拍个照便将头发复原。 显然,杀马特已经回不到当初的盛况,但保留这份珍贵的回忆,是大部分杀马特的唯一念想。 每一种文化的出现,都不是偶尔的。 不同时代背景下,总会催生出新的不被大众认可的群体。 正如罗福兴所说:“即使我没有创造出‘杀马特’,这个群体还是会出现”。 对钟爱杀马特的人来说,那是独属于那个时代的他们,唯一的精神慰藉。 他们之所以不管不顾地相拥在一起,是因为只有和他们一样的人,才能让他们找到生命中缺失的那一块。 “有时候感觉这个头发给了你一种勇气,从形象上就有一种震慑的东西。” 罗福兴的这句话,诠释了杀马特的真实心境。 只有让自己看起来坏坏的,才能避开伤害。他们曾这样天真地认为。 事实上,只有自己真的强大起来,才能降低被伤害的可能。 我想,这个道理,他们在多年的成长中已经顿悟。 唯一庆幸的是,他们这样的人群,总是受伤,却从不伤人。 或许,在世俗眼光里,他们只是时代变迁下的“跳梁小丑”。但即便被全世界唾弃,他们依然在自己有限的认知里,努力生活,坚守善念。 光是这一点,他们已经赢了大部分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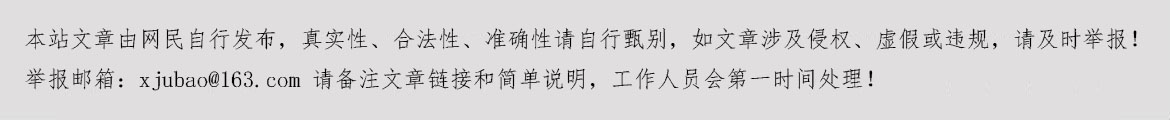
|
|
10 人收藏 |
 鲜花 |
 握手 |
 雷人 |
 路过 |
 鸡蛋 |
收藏
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