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阅
|
亲子鉴定价格 赵珩认为自己就是安徒生笔下《坚定的锡兵》中的那个孩子。他在过生日的时候收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批锡兵,随后陆续扩充起自己的锡兵军队,在父亲的书房中“排兵布阵”,甚至同访客讨论起“战术安排”。 早年间得到的锡兵早已不知去向,然而赵珩的锡兵情结仍然未减。他在法国的圣马洛见到了和小时候一模一样的锡兵,可惜橱窗上挂着“星期天休息”,徒留遗憾离去。 本文选自赵珩作品集《一弯新月又如钩》。 01 坚定的锡兵 孩提时代有过许多玩具,直到今天仍然念念不忘的,要算是锡兵了。 安徒生写过一篇童话,叫作《坚定的锡兵》: 从前有二十五个锡做的兵士。他们都是兄弟,因为他们都是从一个旧的锡汤匙铸出来的。他们肩上扛着毛瑟枪,眼睛直直地向前看着。他们的制服一半是红的,一半是蓝的,但是非常美丽。他们待在一个匣子里面。匣子盖一揭开,他们在这世界上所听到的第一句话是:“锡兵!”这句话是一个孩子喊出来的,他拍着双手。今天是他的生日,这些锡兵就是他得到的一件礼物。他现在把这些锡兵摆到了桌子上。 我想,我就是安徒生说的那个孩子。 当我过五岁生日的时候,我得到了属于我的第一批锡兵。那是父亲小时候玩过的,大约是1930年前后在天津租界的洋行里买来的,而这些锡兵的生产年代则是1919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第二年,是英国制造的。我的老祖母总喜欢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之为“欧洲战事”,因此我在小时候只知道有“欧洲战事”,而不知道有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些锡兵装在一个木匣子里,并不是二十五个兄弟,而是三十七个。据匣子外面的文字,不但写着出品年代,还标明装有四十个,其中三个是在父亲小时候弄丢了。 这三十七个锡兵也蔚为壮观,是真正锡铸的,高约六七厘米,每个都有四十克左右,分为三种姿态:一是站立持枪的,一是半跪姿射击的,一是匍匐姿态射击的。通身深橄榄色,造型十分生动,军装的折皱,佩戴的子弹盒,甚至马裤下部的扣子都十分清楚。立姿的锡兵身后都有背囊,肩上扛着毛瑟枪,那枪杆很长,上面还有刺刀,由于伸出部分过长,就容易损坏,当这套锡兵到我手里时,有三四个立姿士兵扛的枪已经没有枪管儿和刺刀。我历来有个“光复旧物”的习惯,若干年后,终于找了个焊洋铁壶的到家里来,比照一个完好无损的锡兵复制了枪管儿和刺刀,那工匠手很巧,居然做得天衣无缝。 与这套锡兵同时的还有一门克虏伯大炮,那炮与锡兵并非是配套的,是用铁皮制造,外面有迷彩漆,远比不上锡兵那样厚重。炮也是父亲小时候玩过的,同样是在“欧洲战事”以后出品的,但是德国制造,大约也是从天津洋行中买来的。那炮闩可以拉出来,炮膛里装有火石,一按炮闩,炮口就能打出火来。又过了许多年,我的儿子也玩儿上了这门大炮,一件玩具经历了祖孙三代,大概也是不多见的。 自从有了这套锡兵,一发不可收拾,总有“扩军”的念头。当时的玩具店有卖小铅兵的,质量很差,大多为铅制,模子里倒出,整个是扁的,毫无立体感,只有两厘米,放在手里轻飘飘的,形象也模糊不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不少私营小店,尤其是在东安市场和隆福寺后边,还存在一些“老虎摊儿”,卖些旧洋货。某次随母亲逛隆福寺,终于发现一套制作精良的锡制骑兵。 这套锡骑兵大约有二十多个,大小和分量与英国锡兵差不多,全部骑在马上,威风凛凛。穿着拿破仑时代的制服,上身是白色双排扣的短衣,下身是红色镶有金线的马裤,头戴高筒式帽子,腰间挎有长剑,枪斜挎在背后,与那套锡兵虽不是一个时代,但很是配套,只是一为彩色,一为橄榄色。摊主索价二十元(当时一幅齐白石的画也仅值二十元),我们让他放在柜台上,然后一个个摆出来,简直漂亮极了,虽也是二三十年代的出品,但锡兵的外观很少磨损。母亲与摊主讨价还价,那人低于二十元不卖,我摆弄许久,只得随母亲悻悻而去。 二年级升入三年级的期末考试我很用心,语文、算术都考了好成绩。拿回成绩单的那天,母亲很高兴,从她的房间拿出一个装巧克力糖的纸盒子,我以为她奖励我一盒巧克力,打开时,我惊呆了,竟是那套我梦寐以求的锡制骑兵!那种兴奋的心情,至今难忘。 步兵和骑兵都有了,又开始企盼军中辎重。后来又陆续买到了两三种国外出品的炮和当时国内制作的坦克车。那些火炮中有十六世纪欧洲长管炮,这种炮的炮管较长,口径较小,是发射霰弹用的。也有十七世纪以后的榴弹炮,这种榴弹炮大约在全世界使用了近二百年,开始炮管较短,口径较粗,十九世纪以后变为炮身长、口径小,但射程却很远,射角也远远大于早期的榴弹炮。同时我也有早期的加农炮和拿破仑时代的山炮、野炮,各种各样大约有十几门,时间跨度达四五个世纪。其中许多炮是家中的朋友送的,他们知道我喜欢玩儿这类东西,于是变着法搜罗来送给我,其中有一两门简直就是真炮的小模型,超过了玩具商店的商品。 后来东四信托商行的老茹送给了我一套可以衔接铁轨的小火车,是他们商店在门市上收购来的,也像是三四十年代国外出品,大约有十段铁轨,可接成一个圆弧形,有火车头、车厢和货车等四节,将车头的发条上紧,火车头就可以带着车厢跑起来。此外还有扳道房、车站、山洞和信号灯什么的。 我最早看见这种东西是在外祖父住宅弘通观院子的南头费家,也就是后来的社会慈善活动家费璐璐女士的父亲家。我那时四五岁,每到费家,总会舍不得走,因为他家总有个玩具展览,最令我好奇的就是一整套电动小火车了。当然比后来老茹送给我的还要壮观,占地面积可达七八个平方米,火车和车厢既大也长。费家好像也有不少锡兵,只是当时没有太注意罢了。 02 被熔成了一个锡球 老茹的一组铁路运输玩具使我的军阵整体化有了新的延伸,锡兵从此派上了更大的用场,玩法也有了不少翻新的花样。 我首先将母亲的精装洋文书从书桌上搬下,搭成城堡或峡谷,铁道和火车置于峡谷和城堡的一侧,站台和扳道房、信号灯下都布置些站立的锡兵,而将那些跪射和卧射的锡兵置于峡谷之上,做伏击状,骑兵则从峡谷驰出,形成一支浩荡的马队。然后再随意布置变换,口中念念有词,这样可以玩上整整一天。 那时玩儿这套东西需有较宽敞的地方。开始选择在饭厅,可到了开饭的时候,这些费尽心机布置的战阵就必须撤去,偃旗息鼓,另作图谋,让我十分恼火。后来我挪到父亲的书房去玩,那时父亲工作很忙,在家的时候不多,倒也无人打扰。 以后的几年中,我又在东安市场等处买到些小套或零星的各种锡兵,从其军服看,有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有英法百年战争时期的,有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有拿破仑战争时期的,也有普法战争和“一战”时期的,但其大小和品质都差不多,均为锡制。凡此五花八门,大约有锡兵近二百众。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东安市场的工艺品摊上出售一种泥质骑马小人,多以三国人物为主,如曹、孙、刘和关、张、赵、马、黄等,以及周瑜、典韦、许褚、张辽、黄盖等等,可以有四五十个品种。全是泥塑彩绘,袍服铠甲辉煌,骑在马上,那马腿是四根铅丝制成的,立得很稳,大小与铅兵差不多,当时价格是一角五分至二角(今天仍可以在工艺品商店买到,稍大于五十年代的,做工粗糙,已经卖到每个二三十元)。我当时布阵正愁有兵无将,那些锡兵都是一样的军服,看不出官兵之分,这种骑马武将正可将兵。后来我几乎买全市场上能见到的骑马人,于是完全以三国故事为原型布阵,从而改变了战争格局。 天下三分,自然有了三支队伍,骑马人是以魏、蜀、吴归类,绝不含糊,但所率的锡兵都是外国人。那些锡兵脚下都有个锡托儿,立得很稳。随于鞍前马后者,皆为英、法、德、美不同时期的士兵。我那时把战阵扑腾得也最大,地方不够,就从桌上搬到地上,依然以洋装书为主要筑“城”原料,还自己做了十余面旌旗,上书魏蜀吴和关张赵马黄等人的姓氏,立于“城”端。至于哪里对阵,哪里设伏,哪里阻击,哪里屯兵,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一间屋子可以全部摆满,场面十分宏大。如果赶上收音机里播出连阔如的评书《三国演义》,随之变换格局,更是有了创作的源泉。每当此时,似在建安黄初之际,身于万马军中,那种快乐难以言表。 那时家中的卫生间在父亲书房的南侧,要从祖母的正房去卫生间就要穿过父亲的书房。每当我在父亲书房中“布阵”,祖母和来客总是叫苦不迭,要蹑手蹑脚穿过我的战阵,实非易事,后来干脆大家从院中绕过西厢房,不愿在那里步营蹈阵了。 也有些来客愿意看我玩耍,驻足观望或指指点点,问这问那,如遇我正玩得高兴,也愿意与他们说说我的“军事战术”。更有好事者,指指两摞书中间问道:“这是干什么?”我说是子午谷,山头设伏,可以夹击入谷来军。那客人就说:不好!你的谷前谷后都是开阔地,虽遇伏击,仍然可进可退,你当在前有阻击、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居高临下伏击敌兵的目的。”然后一定要看着我在洋装书的两侧摆上一将和若干锡兵,才算罢手。也有来客说炮射弧线,只能摆在平地;屯兵不要在山上,如敌断其水源,则大势去矣。凡此自以为是的客人皆为男性,家中来的女客对我这些勾当是不屑一顾的。 我将这支跨越时空的杂牌部队玩了四五年之久,乐此不疲。就是在睡梦中,也会梦到我的锡兵走动了起来,按照我给它们排列的位置,忠实地恪尽职守。至于“铁马冰河入梦来”,那是常有的事儿。 我的锡兵和那些小骑马人都早已不在了,尤其是那些锡兵,应该颇具些文物价值了,不知道今天它们在哪里?安徒生写的那个一条腿的锡兵最后被丢进火里,溶成了一个锡球,这是我小时候读《坚定的锡兵》时最伤心的情节。 03 橱窗内一模一样的锡兵 我的锡兵情结延续至今。一位年轻朋友前几年去法国,曾在卢浮宫附近给我买回两个骑马的锡兵,从外观看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旧货,形象很生动,但做工远不如我小时候那一组拿破仑时代的锡骑兵,掂在手头的分量也轻得多。后来我去法国时才知道,就是在巴黎搜寻这样两个锡兵也不大容易。现在法国店里卖的,大多是树脂做成的,很粗糙,颜色也很恶俗。好的锡兵却做得体积很大,成为一种装饰性工艺品,而且价钱卖得很贵。 2005年我在法国卢瓦尔河谷的香堡(Chambord)内看到了一组波尔多公爵孩提时代的大炮和锡兵,那大炮和辎重做得却十分精致,体积也比我小时候玩的大许多。除了炮之外,还有岗亭、弹药车、枪械车等等,锡兵是彩绘的,个子也大,完全是贵族气派,但我并不十分喜欢,总觉得还是小时候我那些英法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锡兵做得好。 无论是在巴黎的街头,还是在布鲁塞尔的小巷,每逢有玩具店或工艺品小店,我都会进去看看有没有小时候玩儿的那种锡兵,在这些地方流连忘返,以至于耽搁了不少时间。我发现偶有武装小兵,基本上也是树脂做的,而且几乎都是中国制造的。 后来在巴黎歌剧院附近的杜特大街(Drouot)发现了一家锡兵专营店,里面的锡兵做得不错,但形象都是中世纪的武士,身穿铠甲,手持刀斧和盾牌,问问价钱,每个都要三四十欧元,我相信那些锡兵出品的时间绝对不会超过十年。杜特大街上还有两家锡兵店,橱窗摆得很漂亮,有成队的锡兵和军乐队方阵,军装很华丽,制作也很精致,就连马靴上的马刺都能看清楚,然而这种军队是不能作战的。进店去看看,老板很热情,他说这些锡兵都是西班牙做的,要成套卖。我没有打听价格,相信一定是非常昂贵的。 我在法国仅仅买回一门大炮,那是在巴黎荣军院(即拿破仑墓)买的。这种炮的炮身在哪里都能见到,当然是从前膛装炮弹的那种,但是大多没有炮架,因当时的炮架或为木质,或为铁铸,木制的早已朽烂,铁质的也移作他用,在荣军院的走廊里竖立着许多这样的炮身,而完整的大炮却仅在四角各置一门。我买的那门炮大约有一公斤重,是有着庞大炮身和车轮的那种,炮身上铸有“N”的标志,显示出拿破仑时代的特征。我想那应该是滑铁卢大战时代的兵器。 巴黎荣军院内有法国最大的军事博物馆,展示了从古代到“二战”时的各种铠甲、军服和兵器,最令我驻足不前的就是那些身着甲胄的模型。也有从路易十三到拿破仑三世各个时期的军装,都穿在真人大小的模型身上,这就是我那些锡兵的原型,可见那些玩具锡兵都是仿照不同时期军装服饰铸造的。展览中也有我没在锡兵中见过的,例如法国大革命(1789—1793)时期的军中女酒保,正是像雨果的《九三年》中描写的那样。再有就是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最早的装甲兵和防化兵,在我的锡兵中都是不曾有过的。我仿佛又置身在锡兵的世界,在我的眼中,它们是放大了的锡兵队伍。 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与小时候玩儿过的那种一模一样的锡兵,那是在法国东北部诺曼底小城圣马洛(Saint-Malo)见到的。 圣马洛历来有“海盗城”之称,面对英吉利海峡,是中世纪海盗盘踞的地方,城的一侧筑在海水中,另一侧与大陆相接,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小城。可惜古时的圣马洛毁于“二战”炮火,今天能见到的只是重新修复、以供游览的圣马洛了。这里虽是旅游胜地,却有着非常浓厚的生活气息,小城中有万余人口,有石板铺就的街道,屋舍俨然,商肆栉比,我们到圣马洛恰逢星期天,上午人们大都在教堂做礼拜,街上很少有店铺营业,咖啡馆的伙计方才懒洋洋地摆出阳伞和桌椅。高低不平的小街两侧,留给人们观瞻的只有五光十色的橱窗。 圣马洛与英国只有一水之隔,深受英国文化的影响,店里有漂亮的英国瓷器,不乏威茨伍德的出品;有各种花边和十字绣,也有各色各样的小工艺品。走过每家小店,都可以停留下来欣赏橱窗里的陈列。猛然发现一组锡兵,与我小时候那套英国锡兵完全一样,我相信他们是孪生兄弟,从那些锡兵身上斑驳的痕迹,也能看出是二十世纪初的出品。我站在橱窗前久久不肯离去,无奈地望着玻璃门上挂着“星期天休息”的纸牌子,最终带着遗憾离去。 04 锡兵想“她能做我的妻子” 也许是遗传的缘故,儿子小时候也喜欢摆兵布阵,除了那门克虏伯大炮之外,他没有玩儿过真正的锡兵,只有很多塑料的小兵,百十个小兵放在一个盒子里,也没有多少分量。但他的军队却是现代化的,除了二十余辆汽车、救护车、坦克、装甲车外,还有十余架飞机。他的玩法与我大致相同,能在他爷爷楼上的书房中玩儿一天,没有任何声响。寒暑假中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趴在地上摆弄千军万马,有好几次爷爷奶奶忘了叫他吃饭。我曾给他做过一个很精致的城堡,是用硬纸壳糊的,最精心做的是吊桥,那吊桥用一块纸板刷上胶水,又将树枝剪成同样长短的小棍儿,一根根像枕木一样粘在有胶的纸板上,桥头安有绳索,可以慢慢拉起。我如果能把父亲小时候玩儿过的锡兵留给他,那该是多有意思的事。 安徒生关于锡兵的童话结尾,是那个少了一条腿的锡兵经过了种种周折和旅行,最后回到了它原来待过的地方,看到了以前那个小孩,以前那些宫殿和玩具,还有他心爱的舞蹈家。五十年时间,我一直没有忘却我那些可爱的锡兵,梦想着他们有一天又能回到我的身边。 五十年前,家里来了一个小女孩儿,她是随她的妈妈来做客的。当她独自踱到我的锡兵军阵前,好奇地睁大了眼睛,她从来没有看到过那样壮观的锡兵队伍,于是她向我问这问那。我有些不耐烦,忽然间突发奇想,告诉她小兵会自己走路,请她出去一会儿,奇迹马上就会发生。她将信将疑地转身出去,不一会儿回来后,发现桌上的锡兵们果然已经改换了位置。但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那几个锡兵是自己走开的,这成了五十年来我们之间的一段公案。 这个小女孩儿多少年来一直忘不了这件事情,她就是我的妻子。 本文节选自 《一弯新月又如钩》 作者: 赵珩 出品方: 领读文化 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20-12-1 页数: 352 编辑 | 白羊 主编 | 魏冰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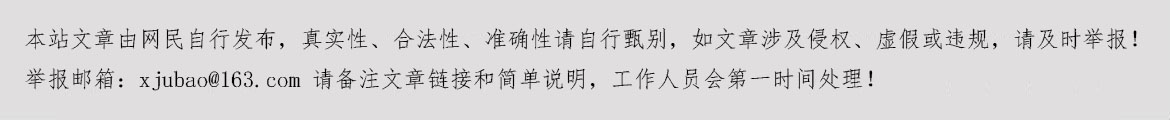
|
|
10 人收藏 |
 鲜花 |
 握手 |
 雷人 |
 路过 |
 鸡蛋 |
收藏
邀请